疫情之后,全球化会何去何从?
2020-03-24 10:49:44风声 来自北京市
文丨特约评论员 连清川
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撕开了早就破败不堪的全球化的帘幕,令人们看清了光鲜的经济增长、互联网迷梦和技术发达背后的人类劣根性。
新冠肺炎继续在全世界蔓延,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病例。只有在电影《生化危机》中才能看到的世界地图快速染红的局面,竟然变成了真的:没有僵尸,是人类在任意地侵袭自然之后的反噬。
每天的消息都是混乱和令人恐惧的,而在政治层面上的摩擦,更加使人们悲叹于这场疫情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和议员们在不同的战场里互殴,指责对方破坏抗疫,缺乏联邦政府统一指令的州和县各自为政,令人怀疑美国是否能够有效防止扩散;欧洲各国的政策宽严不一,意大利铁腕锁国,而英国和瑞典则“佛系抗疫”;团结是不可能的,3月7日,瑞士媒体报道一辆属于瑞士公司的卡车在前往瑞士途中被德国海关拦截,车上有24万个防护口罩。11日德国再次扣下了瑞士从中国进口的一批外科手套,当天,另外一个瑞士邻国意大利也扣了瑞士的一批医疗物资——消毒水,看得出来彼此的恐慌。
经过了数十年的全球化,彼此的磨合、贸易、人员的交流、知识的交换,甚至是政治经验的彼此借鉴……一夕之间,全都崩塌了?这是怎么了?
疫情暴露了全球化的真实处境
但是,起初,它就已经悲伤地预告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1月20日,钟南山博士的惊天一呼;1月23日,武汉封城。
2月18日,韩国出现“第31号患者“,也就是后来被称作”超级传播者“的确证,开启了大邱市的噩梦,同时也开启了国际疫情的大幕。
紧随其后的,是日本、意大利、美国、西班牙、德国……
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几乎处在一个孤军奋战的过程中。并不是说,其它国家全都坐视不理,的确,从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的援助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但是它那个时候在整个世界的概念里,仍然仅仅是事不关己的“人道主义“援助。
一场火灾、地震、海啸之后的援助,是人道主义援助,因为这些都不会蔓延。
但是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没有一个国家把这场危机当成为可能会危及自身的全民性危机。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冠疫情列为“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PHEIC),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正儿八经地开始进行有效的防范。马照跑,舞照跳,口罩看不见,大型公共场合集会和宗教仪式都照常进行着。
中国人被孤独地禁闭在家中,宛如世界中的一片孤岛。而整个世界依旧灯红酒绿,舞榭歌庭。医学界声嘶力竭,而政客和民众置若罔闻,“各自欢喜”。
3月7日,权威的《柳叶刀》杂志发表社论,抛出WHO专家组对中国的考察报告,指出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控制了疫情。而整个世界实际上都可以从中国的经历中,学到对疫情控制的经验。这篇文章的标题是:《COVID-19,太少,太晚?》
的确,已经太晚了。当时,韩国日本都已经沦陷,意大利的数字每天以几何级在增长。到现在,也不过才半个月时间,却像这病毒已经肆虐一年,全球飘红。

WHO备受争议,许多评论家称之为“宛如僵尸”。可它也实在冤枉得紧,它已经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连续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并且快速提高了预警的级别,不断在中国近距离观察和记录。它还能做什么呢?
它不是权力机构,它无权给任何一个国家下达禁足令,无权要求任何一个国家调配抗疫物资,甚至,无权指导任何一个国家做任何一件事。它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信息机构而已。
在公共卫生这个领域里,包括在所有需要政治权限的领域里,全球化根本没有监管,无从统一行动,并且对于几乎任何一种危机没有一个能够进行协调的协作机构。没有一个国家会让渡自己的权力,让一个国际化的共同机构来对自己指手画脚。
经过了30年不遗余力的全球化,整个世界的流动性如此之大,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人员与生物交换如此频繁以至于导致了多次的物种灭绝,而且在已经有了埃博拉和MERS几次大型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依然如此漠然与颟顸,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就是这么发生了。一场疫情,掀开了全球化真实处境:原来,以往的全球化是单一的、经济层面上的全球化,而已。
“巴别塔”的思想困境
人们大概已经忘记了,全球化曾经有个更长的名字,叫“全球一体化”。它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分工与合作的全球化,而是更广泛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体化。它肇始于1989年,意识形态的对峙结束,国际间大战的风险解除,军备竞赛再无必要。于是人们开始赤足狂奔:在经济上。
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场裸奔。强健了的,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然在旧的躯壳中。头重脚轻的奔跑,必然要摔一大跤。
连欧洲人大概也都已经忘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体化实践,是法国总统顾问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哲学实践:欧盟。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
在科耶夫去世之前3年的1965年,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他似乎可以含笑九泉。
但是,欧共体直到今天的欧盟,离科耶夫的梦想其实都有点远。他所要建立的共同体,其实是一个哲学概念,叫“普遍均质国家”,大致的意思是在这个共同体之中的国家,在价值观、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经济形态上,都十分接近。欧共体的目标,就是让所有国家之间,拉平彼此的差距。

科耶夫的本业是哲学家。当然,他的理想是建立在所有前人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从康德到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加令人恐惧的意识形态对峙,地缘战略思维出台,世界似乎成为了零和游戏的竞技场。
所以,科耶夫要为世界缔造出一个非零和游戏的新生态。
可是柏林墙倒塌了,世界和平了,全球化开始了。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哲学和理论了。
只有两个浅薄的理论甚嚣尘上,试图解释世界: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和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亨廷顿认为,全球化将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斗兽场;而福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了,世界只剩下了自由化民主一种可能。
可是绝不能拿“文明的冲突“简单定义中美间的竞争,比此更根本的,是经济地位的争夺;欧洲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有竞争冲突吗?福山也有其荒唐一面,要不去和塔利班聊聊自由化民主?
人们开始以为自己建设的是《圣经》里曾经说的巴别塔,一座能够通向上帝的人类登天梯。
可惜,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连科耶夫这样的哲学家都没有了。柏林墙倒了,世界上没有对峙,没有了冲突,没有了战争威胁,人们缺少了一个可见的敌人。
除了经济发展,整个世界好像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没有政治的理想,没有幸福的方向,没有人类大同的可资追求的目标。赚钱,发展,成了惟一和可行的关键词。
可是啊,科耶夫的“普遍均质国家“也已经破产了。英国退欧了,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正在涌入,东欧和土耳其在发展的落差中心怀怨怼。
既没有竞争的哲学思想支持,也没有合作的哲学思想支持,全球化的理想好像一艘方向不清的航船,前途免不了礁石和风浪。
万世开太平仍是美好的理想
能够造成世界性危机的,不只有新冠病毒这一场而已。这只是一场大型演练。能够毁灭人类的风险其实一直笼罩在地球之上。非传统安全因素,这个陌生而拗口的词语,已经讨论了许多年。
尽管这个词有许多争议,各个国家也都有着自己的解释,但以下几个部分,是普遍认可的:恐怖主义、气候危机、公共安全,以及近几年开始逐渐成为显学的网络安全。
恐怖主义当然不仅仅发源在中东。那是好莱坞电影的套路而已。西班牙的巴斯克分裂主义,孟加拉国泰米尔猛虎组织、尼泊尔的毛派,都属于恐怖主义,当然,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无差别杀害,不分军政人员和平民,是他们的杀戮特点。
《京都议定书》旨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分配碳排放的配额。但是美国退出了这个国际协定,而各个大国也各有算盘。
公共卫生危机,这次疫情,让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问题摆在面前再清晰不过了。可是从民间到政府,没有人会在意这些正在不断放大和极端化的事态。联合国主要解决战争问题,WTO主要解决贸易问题。
WHO是个无权无势的小白机构,气候问题连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恐怖主义就是打仗,网络安全就是吵架。
哪有一个协调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权威、力量、资源和预算来解决这些问题?大数据、AI和机器人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词语。全球性的网络协议瞬间传檄而定,大数据的标准想来并非难事。非传统安全?边缘化的小事而已。
随波逐流的全球化便如此这般越漂越远。人类的共同福祉,我们生活在其上的地球的命运,以及冲冠一怒大杀四方的恐怖主义,如同今天正在肆虐的病毒一样,愈演愈烈。
缺乏共同方向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只有在赚钱这件事上最有合作的可能性:全球化的供应链分工,物流的普遍性通畅,技术人员和知识阶层的流通,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配置。
但是骨子里,人们还是竞争性的。所以一旦全球化触碰到了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时候,篱笆和城墙在瞬间就树立起来。地缘战略又重回台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民族主义从19世纪诞生之后,一直就主宰着世界各国的主流话语。竞争和厮杀才是常态。合作总是困难的,需要磨合的,而对峙和敌人只需一句话的龃龉,只需一场利益分配的不均,甚至,只需一群人的振臂一呼。
奢求一种能够协调全球性共同利益的机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发展阶段的差异太大,生活方式的水平相距太远,而各国之间话语权、资源占有率和历史民族文化的分歧太庞大,太复杂。每个国家都想执牛耳,发号令,怕吃亏,占便宜。
疫情如火如荼,不过终究会平息静止。在当下世界的医疗卫生水平之下,控制这场烈度并不高的公共卫生危机,仍然可以实现。只是时间和代价的问题。
在缺乏共同行动和共同认知的基础上,时间很长,代价很大。
但这确实证明和提醒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全球化,令整个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是一个后现代问题,并不因为落后而产生的危机;它是一个后地缘战略问题,不能依靠彼此切割,而要依靠彼此合作;它是一个后竞争性问题,不是谁能够率先占领优势,而是如何变成共同解决方案。
然而,再一次事与愿违。它还是演变成了前现代问题:所有国家都短缺物资;一个地缘战略问题:各自隔绝,拒绝合作;一个竞争性问题:看谁能够率先研制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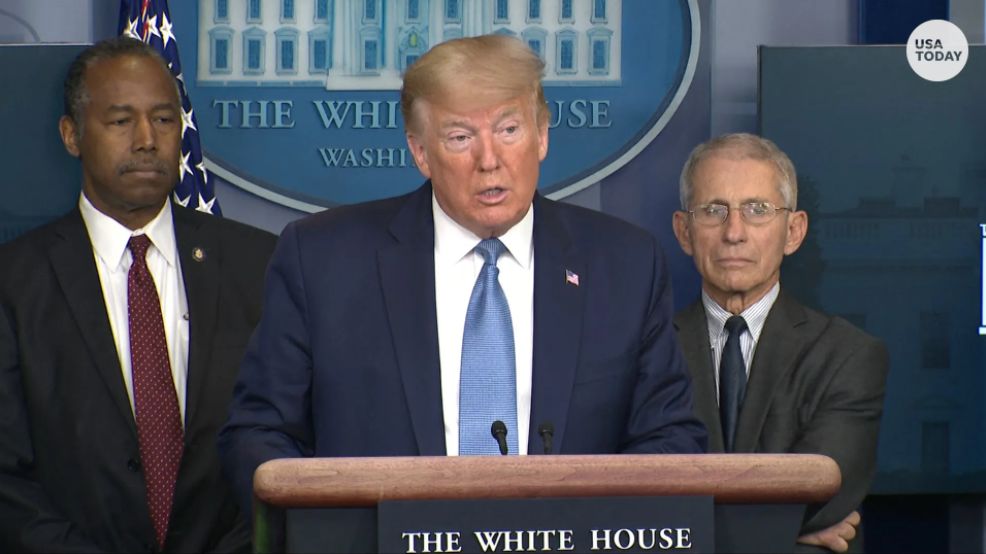
这个分崩离析的局面,总有一天会被各个国家的权贵阶层和领袖政要所认知:当他们也被置于风险之中时,他们会压迫政治层面,拿出解决方案。
在疫情之后,世界会面临两个方向:要么各个国家自行控制疫情,地缘战略依然盛行,民族竞争和对峙,成为主流国际交往方式;要么在彼此合作中找到方法,进入全球公共议事时代,指定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全球的公共事务。
笔者实在没有科耶夫那么乐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在2000年倡议提出了《千年宣言》,发愿消除贫困,减少疾病和保护环境,被誉为“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但是20年过去,其中没有一项愿景,曾被实现。
普遍均质的欧洲尚且在遥远的远方,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均质国家,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病毒没有分别心,对政要、富贵、贫病、美丑、老幼都一视同仁地残忍。但人类有差别心,并且很强,而且存续了数千年。在对付病毒这件事上尚且不能搭一个万众一心的巴别塔,更遑论其它。
笔者倒是心心念念了许多年,期待一个全球化时代伟大的哲学家出现,能够告诉人类在这个史上罕有的长和平时代中,这个世界应当以何等的心胸和行为,迎接未来,不再重堕战和的罪恶轮回。但如同这般的圣人天才,该有怎样的机缘,才能出现啊。
这么说,显得我很是迷信谶纬,期待奇迹,这很不科学。但是如果人类对于一个时代的状态,没有共同的认知、方向和理想,怎么可能去同心同德去建设一个共同福祉的社会呢?
怪只怪我们这个全球化太年轻了,还很脆弱和稚嫩,连一场小小的发烧咳嗽和肺炎,都能够影响全球化的发展。
新冠病毒的全球肆虐或许也是一个契机,可以让我们重新打量几十年来全球化的发展,重新思索世界需要何种全球化?放弃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口号,回归目前世界的真实局面。一个依靠国家共同体来塑造的全球化,离不开国家共同体的私心和利益。全球化的未来到底如何?就从这次疫情开始,好好想一想,未来从此刻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