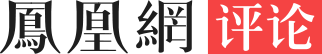高明勇:“人文”如何“经济”,“经济”何以“人文”


独家抢先看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最近,与几位学者开会时谈到“人文经济学”的话题,大家知道我担任“醴陵城市观察员”,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我,如何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醴陵?我说这个题目从去醴陵调研前就已考虑,但一直“动念”,却未“动笔”。
原因何在?我讲了一个流传很久的“段子”,“要与文化人谈钱,与商人谈文化。”这个段子可以有多种解释,较有共识的解释是,做事要有针对性,“被需要的”才是“有价值的”。言外之意,“文化人”更需要“钱”,“商人”更需要“文化”。通俗理解,文化人代表着“人文”,商人代表着“经济”,从需求的层次看,“人文”和“经济”应该有更多的适配性和可能性。当然,现实中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有些“文化人”对“钱”有兴趣,但看不上“商人”,有些“商人”对“文化”有需要,但也看不上“文化人”。
我更倾向于“行动研究”的视角,“以社会改进为目的,强调行动者做研究,在行动中研究,为行动而研究”(《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凯西·卡麦兹著,边国英译,陈向明校,重庆大学出版社)“研究者不应用方法来限定问题,而应具有‘问题意识’,让‘真实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得到适当的定位,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方法。”
其实,从醴陵出发,结合“人文经济学”的地方实践,分而析之,反而可以提供更多的启思。
01何为“人文”,如何“经济”
虽然目前“人文经济学”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但也因此有了更大的阐释空间。“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与江苏省密切相关,在江苏,相关的实践与研究可资参考。作为经济学家的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与其他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教授一起,以无锡为研究对象,推出《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则以苏州为研究对象,书写出《经典之城:苏州人文经济发展三部曲》。而苏州和无锡,都是通常意义的“江南”代表。
与此同时,在岭南也有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公开资料显示,在顺德的官方口径中,“人文经济学”既不是立足人文说经济,也不是着眼经济观人文,更非人文和经济的机械拼盘、物理链接,而是彼此生发、两相融合的化学反应。就顺德的现实来看,“既不是放弃制造业搞文化,也不是只抓经济忽视精神需求,而是找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对人文价值的关怀、发展、利用和满足,让各种资源要素使用效率最大化、生活品质最佳化和城市治理能力最优化,从而让文化软实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从江南到岭南,从经济学家到文化学者,不同的诠释,也说明了人文经济理论概念与实践形态的内涵丰富。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文化经济学”。长期以来,更为常见的是“文化经济学”,流传更广泛的说法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以经济为主,文化为辅,以经济为目的,以文化为方法,在特定阶段,这一现象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也蕴含不少隐患,比如极端的做法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方法”,哪怕牺牲“方法”。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文旅经济学”。随着文旅行业的蓬勃兴起,不少人容易把“文旅”等同于“人文”,或许“文旅经济学”可以算作“人文经济学”的一种形态,但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对垂直,也相对窄化,仅就经济形态而言,“文旅经济学”也相对简单。特别是现实中,“旅”有余而“文”不足的现象并不鲜见。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文创经济学”。不少人容易把“文创”简单理解为“人文”的载体或表征,“文创经济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容易被狭义地理解为“人文经济学”。事实上,“文创经济学”更多的是“物”的经济学,或者“文”的经济学,而“人文”的含金量远不止于此。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人本经济学”。曾有学者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人本经济学”的概念,如常修泽教授认为,横向上,指全体人;纵向上,指多代人;内核上,指多需人。或许二者之间有交叉重叠,但并不能简单画等号。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人类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人类经济学”的概念,且不说“经济学”能否解释或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就其本义,是关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概念本身的容量也决定了“所指”的无限。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人工经济学”。当AI铺天盖地,当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的新宠,不少人容易将“人工智能经济学”理解为“人文经济学”,人工更侧重“技术”层面,而人文更侧重价值观层面。
概念的界定,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区分,有助于理解何为“人文”,如何“经济”。
02人文经济,何生“江南”
一个值得追问的话题,为什么“人文经济学”的概念产生于江苏?或者说是产生于“江南”“南方”?
一则史料可为佐证:明成化四年(1468年),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说:“苏为郡,甲天下,而其儒学之规制亦甲乎天下。是盖有泰伯至德之化、子游文学之风、安定师法之传在焉,不徒财赋之强、衣冠之盛也。”又说:“使世之论者,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
从“郡”到“学”再到“人才”,皆“甲天下”,徐有贞认为这些比“财赋之强、衣冠之盛”更为重要。
其实,从更为长远的视角看,“江南”之所以成为“江南”,牵涉到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一般来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起于魏晋,显于中唐,定于南宋。相关研究表明,背后的动力因素很多,社会层面的因素,有战争及其衍生反应,以及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自然层面的因素,包括气候的变化,水文的变化,植被的变化,以及土壤的变化,这些都导致南方更易于生产、生活。
历史学家郑学檬认为,在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中,“技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力因素。一方面,伴随着大规模人口迁移,人才的比重也相应增加,连带着中原地区的技术一并迁移,并结合南方地区的资源,因地制宜,不断实现技术上的更新与迭代,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如何研究、记录并传播这些技术的问题,涌现出不少科技著作。
纵观这些古代科技著作的成书,在朝代分布上有三次密集期的高峰,一次是汉代,如医学上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等,数学上的《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一次是南北朝,农业科技方面的《齐民要术》(贾思勰),水利方面的《水经注》(郦道元)即为例证,另一次高峰就是宋代以及后世的元朝明代,宋代的《梦溪笔谈》(沈括)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元代的《授时历》(郭守敬)则代表了当时世界天文学的最高水平,有“明代三大科技巨著”之称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农政全书》(徐光启)、《天工开物》(宋应星),标志着中国传统科技的最后高峰。以及《徐霞客游记》,也是地理学的高峰。
更值得思索的是这些著作作者的籍贯或生前主要活动区域分布,宋代之前,大多在北方地区、中原地带,如《九章算术》主要编纂者张苍为阳武人(今河南原阳),《伤寒杂病论》作者张仲景南阳涅阳人(今河南邓州),《水经注》作者郦道元为范阳涿县人(今河北涿州),《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为青州人(今山东寿光)。
宋代之后,则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写作《梦溪笔谈》的沈括为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写作《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为湖广黄州府蕲州人(今湖北蕲春),写作《农政全书》 的徐光启属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今上海),写作《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为江西南昌府奉新县(今江西奉新),《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弘祖是南直隶江阴县人(江苏江阴)。
更为宽泛的说,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科技著作的作者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特别是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宋代以后,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
关注这些科技著作的意义在于,其作者不仅要精通技术,也要擅长写作——这种“文理兼修”的特质,正体现了人文与科技的融合,为人文经济提供了历史依据。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也可以联想到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难题”)——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追问可以有很多解释,其中一点因素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技术”多为乡土中国背景下应用转化型的科技,本就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而生。
反观当下,在中国县域经济的转型实践中,“技术”这一关键要素,正以其新的形式,继续发挥着连接人文与经济的枢纽作用。醴陵便是这样一个生动的样本。
03 人文经济,重在“人才”
同为“醴陵城市观察员”的友人王小杨也在关注“人文经济学”这个问题,他撰文分析认为醴陵有三大条件,分别是优越的地理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特色产业。同时,醴陵在实践层面,主要是品牌化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产业升级破解发展瓶颈,以及柔性引才激活经济动能。醴陵在县域发展带来的启示:发现浸润经济的人文新要素,挖掘引领经济的人文新价值,找准驱动经济的人文新赛道,拓展发展经济的人文新业态。(《从醴陵看县域人文经济向何方》,王小杨,醴陵融媒,2025年8月11日)
相对而言,目前诸多研究,大多聚焦“人文-经济”的关系模型,人文如何深度影响经济,经济如何深度融入人文。我想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历程中,需要更为重视“技术”的因素。
就醴陵而言,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产业支柱是陶瓷与烟花。统计资料显示,当前醴陵拥有陶瓷企业1500余家,从业人员近20万;烟花爆竹生产业近200家,从业人员超15万。
这两大产业的共性特点,就是“技术”突出,无论是传统社会的工匠技术,还是现代社会的工业技术,以及绘画等周边性的技艺。可以说,对于醴陵的产业支柱来说,“技术”是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也是参与行业竞争的核心底气,更是应对未来挑战的突破口。
在人文经济层面,“人文-经济”的关系模型也将呈现为“人文-技术-经济”的三元模型。典型的如醴陵陶瓷的“釉下五彩”技术,既传承“人文”审美与记忆,又通过工业化生产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人文-技术-经济”的落地。尤其是当地正积极推动陶瓷与烟花的融合,二者与文旅的融合,不断融合、不断转化的关键点,就在于“技术”。而“技术”的“抓手”,则在于人才。
人文经济的核心,还在于“人”,释放“人的能量”,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生活”。
不断重视人口规模——历史上经济中心的南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的迁移,而一定的人口规模,也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此前城市竞争的重点在于吸引高学历人口,在人口数量增长缓慢的趋势下,城市竞争的关口将不断前移,更加重视人口的流入,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作为依撑,城市的发展必然陷入萎缩的困境。尤其是提振消费,“烟火气”的背后必然是人头攒动。
不断重视人才适配——城市之间不断加剧的人才战已不新鲜,不少城市动辄引进或间接引进“院士”,诚然,“院士”代表着极高的科技荣誉,而对于很多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或行业来说,“院士”未必是刚需,关键在于产业技术适配的人才,比如年初影响一时的“杭州六小龙”,创业团队并没有“院士”参与,反倒是一群年轻人“折腾”出来的奇迹。所以,要不断重视人才适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能调集更多的人才深度参与到城市中来,参与到产业中来。以醴陵为例,比如陶瓷行业的釉下五彩绘画工匠,烟花行业的烟花安全技术工程师等适配人才。
不断重视人文环境——此前,我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调研时,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江南地区对营商环境的重视,政府大楼,企业车间,经常看到“店小二精神”“五星级标准”“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等标语,营商环境的底色就是人文环境,人文经济的基本前提,也一定是人文环境。
人文与经济,并非“搭台”与“唱戏”的关系,也并非“配角”与“主角”的定位,而是彼此滋养、互为表里的共生体。唯有在“人”的土壤中深耕,方能绽放“文”的光彩,结出“经济”的硕果。如此,作为“生意”的“经济”,和作为“意义”的“人文”,才能真正融合起来,转化为内涵式发展动能。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