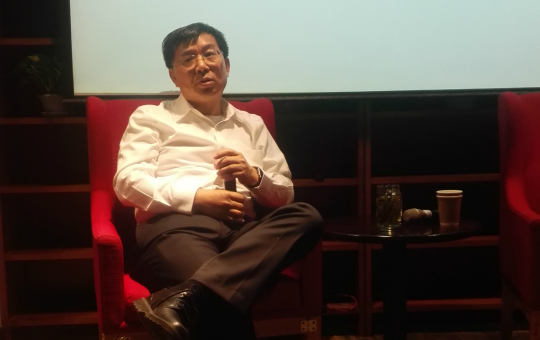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国际史”三部曲:《中国与大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200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战中的华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其英文版,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目前正致力于其“共享历史”三部曲的写作及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享的历史》(已完成。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广西师大出版社拟出版其中文版);目前正撰写《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共享的旅程》(该书系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稿,英文书稿当于2015年中旬完成);其第三部《关于中国:一个共享的历史》仍在研究之中。
前不久,徐国琦的著作《边缘人偶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徐国琦在外研书店就此举办讲座,凤凰网专访了他。

文丨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 张弘
高见:关于中美关系,我此前读过唐启华的著作,里面有一点涉及中美外交,当时威尔逊对中国很友善。
徐国琦:中美外交,2014年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阐述的就是中国人跟美国人的一个共有历史。我们现在看的是中美之间不同等级对抗,实际上历史上来看,美国之所以独立,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要到中国市场来。因为当时美国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地,大英帝国垄断了中国的贸易,美国十三州殖民地的人第一要直接到中国贸易,所以1784年跟英国脱离,独立之后,“中国皇后号”就来了中国。
第二,美国独立时,1763年所谓波士顿茶党事件,当时美国人对英国不满,波士顿倾茶案,它那个茶是中国的茶,所以一开始这个里面就都有联系。
另外就像美国准备独立的时候,美国国父富兰克林,他当时想,美国独立之后,要接受中国的儒家文明,富兰克林说儒家文明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文明。当有人告诉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中国人不是白人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觉得中国人就是白人,这么厉害。
高见:在唐启华的著作中,威尔逊的主张大大激励了中国人,他的声望在中国很高。您怎么看?
徐国琦:我们的研究有一点交叉,但观点不完全一致。1914年到1918年的一战对中国来说是承前启后,非常重要。1912年,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他要步法国和美国的后尘,变成民国?你要看孙中山的内阁、袁世凯的内阁大部分是留学的学生,如外交官顾维钧是留美博士,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是留美幼童,袁世凯的心腹大员蔡廷干也是留美人士。在内阁成员里面,留美背景极强,中国人当时就是要更新换代,要步美国后尘。一战爆发后,1917年8月14号,中国对德奥宣战,是步美国后尘的,因为当时威尔逊作为中立国总统,呼吁全世界中立国仿效美国,而中国一直就想参战,正好等这个机会趁势而起。所以,威尔逊当时发表十四点,民族自觉、平等外交等等,对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事。正因为如此,威尔逊当时在中国被年轻人视为上帝,中国留学生到美国领馆去呼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他的一篇文章公开称威尔逊是世界上头号好人。毛泽东那时候还名不见传的,但是他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就想未来的中国跟美国如果是同盟,那所向披靡。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强的亲美情节。威尔逊当时所谓的新国际秩序对中国非常有诱惑力。
高见:关于蒲安臣,大多数中国读者不是特别熟悉。
徐国琦:1868年,中国第一个出使世界的使团的团长是美国人蒲安臣。他这个人非常好,1861年到1867年是美国对华公使,1867年他准备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总理衙门说,你能不能代表我们出使全世界,他答应了。所以,1868年中美之间第一个和平条约、平等条约是蒲安臣代中国签的。蒲安臣条约为什么平等?第一个它讲究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来往,自由移民、自由来往、自由求学。
蒲安臣是1868年代表中国,先到美国华盛顿跟他的前领导William Henry Seward(西华德)国务卿签的这个条约,然后就到英国、到法国、到德国,然后1870年死在俄国,死的时候49岁,是中国政府的外交官,中国政府的雇员。蒲安臣的墓就在与哈佛大学咫尺之遥的奥本山墓地,钱是中国人出的。
在这些例子中,中美之间没有对抗,当时中国人和美国人互相吸引、互相坦诚,另外也互相支持。
高见:上世纪,另外一个美国人约翰·杜威对中国影响也很大,胡适、冯友兰都是他的弟子。
徐国琦:另外,杜威的学生还有蒋廷黻、蒋梦麟、陶行知等,民国期间都是各方面的领袖。约翰·杜威1919年4月30号到中国,一直到1921年7月份才离开。因为杜威在中国这两年,对他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回到美国之后,他俨然变成了中国专家。1952年,杜威过世,1945年时他都还想到中国来调停国共。
高见:齐锡生、杨天石老师的书里面也有讲到,抗战时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中国比较友善,而蒋介石为何特别厌恶丘吉尔?
徐国琦:中国在一战是极贫极弱的,没人理。二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坚持,使得二战之后中国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当时大英帝国丘吉尔竭力反对,斯大林竭力反对,而美国坚持。因为美国人的坚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强之一,蒋介石当时自己都觉得这个地位变化太大了。一战时,中国是一个极贫极弱的国家,任人宰割,到二战成为四强之一。之所以如此,因为当时美国人不喜欢法国人,法国后来是五强。从中美关系看,这个是剪不断的关联,况且很多方面都是正面的。
高见:因为你是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国,从个人的思想史角度来说,你对美国的认识过程是怎样的?
徐国琦:第一,要从中国近代历史上看,最早的留学浪潮是中国官方组织的留美幼童。1872年,当时的美国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应该说不是首选,因为美国高校比不上欧洲,当时最好的高校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当时的哈佛大学不过是一个小的、不入流的学校。而中国的留美幼童都送到美国去。1872年留美幼童前往美国,1881年召回,120个人。比如说第一任民国总理唐绍仪,设计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刚才我说的蔡廷干也是。留下的一百多人,人人都是各行精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美国当时也是个弱国、穷国,因为1872年美国刚刚结束了内战,正在重建,政治不稳,经济落后,高校也不发达。但就在那种情况下,因为中国人对美国人一种天然的好感和信赖,就派过去。这是第一波留学浪潮。
美国一战时成为世界强国,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随着地位上涨,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个人看,过去中国人有几个误区,就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美国好像是中国的小老弟,但你反过头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有成文宪法最早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有共和国机制最早的一个,美国、法国。中国是1912年才有的。
高见:就你讲的这些,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庚款的退还。我看到特朗普在联合国的演讲,他说美国是向善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一点,您怎么看?
徐国琦:你说的退庚款也是美国人最先。1904至1905年间,梁诚曾敦促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减免部分未付足的庚子赔款。他劝说美国政府,当年庚款要的太多了,远远的超过实际需要,多余的要退回来,美国人接受了。在所有的列强里面,美国是第一个。后来其他国家在各种压力下也开始退,但是不了了之。美国的庚款最有影响,胡适他们都是庚款留学生,3000多人。这些人都是一代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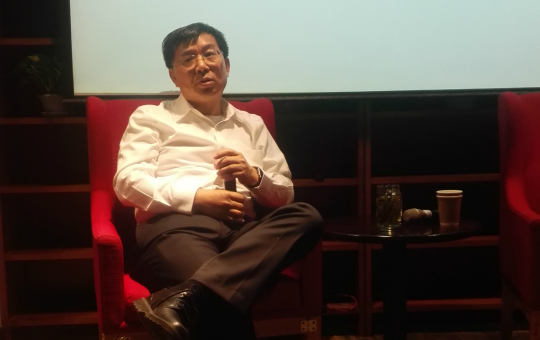
高见:有一段历史,我觉得现在研究的不多,就是黄安年先生出过一个《沉默的道钉》,原来的华工在美国给他们修铁路,然后我读过纳什主编的120万字的《我们人民》两卷本美国史,还有是方纳的《给我自由》两卷本美国史。我注意到里面的一个细节:在美国的这些中国华工,其实受到了很严重的歧视。您怎么看?
徐国琦:不仅是美国对华工歧视。整个从1882年,美国就通过排华法,在法律上歧视中国人。《沉默的道钉》黄安年先生做的非常好,因为这一段就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它做出来了,当时中国人去给美国人建太平洋铁路,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的财富是建立在中国铁路工人的血汗、生命里面。但这一段美国的确是这么多年来没有承认过。吉米·卡特当总统的时候,1979年表示感谢。但是这一段历史,我一直说哥伦比亚大学欠中国人的,就是华工给它修铁路。另外美国还有一个大学也欠中国人的,杜克大学。杜克本人是卖烟草起家的,当时卷烟机发明之后,他就对助手说把我的地球仪拿来,他一看中国人口那么多,如果让中国人都抽烟的话,那他赚多少钱?他能赚无数的钱!于是就向中国卖烟草,中国人的生气被他摧跨了对不对?但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
斯坦福大学最近才终于意识到它欠中国的,中美要联合研究这个题目,现在正在收集资料,因为资料没了,但现在资料很难收。像杜克先生的那些财务,中国人应该找出来或者是中美学者去看,究竟在中国赚了多少钱?你是怎么向中国人推销烟草的?这个不用说坏或者判断或者是要赔偿,我把这段历史给你还原过来,对不对?有很多的这种题目还要做。
《沉默的道钉》,黄安年先生做的非常好,但是资料现在还要进一步整理。因为要写一部好的学术著作,需要很多资料,但是现在非常遗憾,这些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他们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美国的文献资料也从来不重视,因为美国人当时歧视他们,留下的记录不多,现在一百多年之后,我们在想做这个题目,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斯坦福搞这个项目,因为我熟悉他们背景,现在很难做了,因为资料没了。资料没了,你就没法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可以写小说或者什么的,但是不是历史,所以黄安年先生那本书值得尊重。
高见:你自己做的中美共有的历史是求同。现在中美学者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你觉得它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徐国琦:实际上这个一直在做,在西方学者里面,某一个课题的研究很多,比如说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那都是大兵团作战,各方人马在写。它首先不强调你是中国学者、美国学者,看你有没有资格写,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就可以写,就像在2014年剑桥出了三卷版的一战国际史,谁是这个题目的权威,你就写,最后有几十个国家的学者就参与了。学术是不分国籍、不分宗教,就看你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能不能胜任,你写的东西是最尖端、最前沿、代表最新研究水平的。所以在这方面实际上一直在做。
过去我们写中美关系,比如说国内有一个陶文钊教授,他写了三卷本的《中美关系史》,2004年是第一版嘛,现在又出了一个修订本。我们都很熟。过去我们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强调中美对抗、强调中美分歧意识形态。像我刚才提到的中美关系,“共有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就从这个角度给你讲一段,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影响、互相启发的这一段历史。这个可能有的是正面、有的是负面,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像体育。中国体育全运会,实际上跟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系。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在天津设峰会,主要是美国人,然后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后来做过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的王正廷都是这里面来的,这就是体育,通过美国这个媒介过来。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来1984年洛杉矶洛杉矶奥运会上拿的第一块金牌。一些西方政要拒绝出席中国2008开幕式,小布什来了,还待了好几天,这个就是“共有历史”。
高见:最后一个问题,你手头写的第三部关于中国“共享的历史”,这本书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徐国琦:这个就是我的“共有历史”三部曲的最后一卷。第一卷是中美关系,第二卷是亚洲与大战,都是共有。第三部,我想与国内学者像葛兆光、台湾中研院学者王明珂,还有日本神户大学的王珂都在研究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因为他们这些人研究的主要是从中国谈中国,我要从国际的角度,打破国家民族的概念,从上面去看。
高见:从世界史的角度去看呢?
徐国琦:为什么?就像一个人,如果你不跟别人打交道,你叫什么?张三李四没关系。因为你要跟外面打交道。你是中国或者是中国人,所以你要跟其他国家要接触,跟其他人接触,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所以我要从古至今梳理“中国”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但现在我没法告诉你内容,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答案,还正在做。做完了、研究做完了,想法成熟了,可能才有个答案,现在没有答案。因为真正做历史的人,你不能先有答案,只能做完了才有答案。我就算现在告诉你一个答案,也有可能会被推翻,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当初做一战华工,我没有想到它的重要性,等我做完了,我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国际史”三部曲:《中国与大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200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战中的华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其英文版,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目前正致力于其“共享历史”三部曲的写作及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享的历史》(已完成。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广西师大出版社拟出版其中文版);目前正撰写《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共享的旅程》(该书系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稿,英文书稿当于2015年中旬完成);其第三部《关于中国:一个共享的历史》仍在研究之中。
前不久,徐国琦的著作《边缘人偶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徐国琦在外研书店就此举办讲座,凤凰网专访了他。

文丨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 张弘
高见:关于中美关系,我此前读过唐启华的著作,里面有一点涉及中美外交,当时威尔逊对中国很友善。
徐国琦:中美外交,2014年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阐述的就是中国人跟美国人的一个共有历史。我们现在看的是中美之间不同等级对抗,实际上历史上来看,美国之所以独立,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要到中国市场来。因为当时美国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地,大英帝国垄断了中国的贸易,美国十三州殖民地的人第一要直接到中国贸易,所以1784年跟英国脱离,独立之后,“中国皇后号”就来了中国。
第二,美国独立时,1763年所谓波士顿茶党事件,当时美国人对英国不满,波士顿倾茶案,它那个茶是中国的茶,所以一开始这个里面就都有联系。
另外就像美国准备独立的时候,美国国父富兰克林,他当时想,美国独立之后,要接受中国的儒家文明,富兰克林说儒家文明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文明。当有人告诉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中国人不是白人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觉得中国人就是白人,这么厉害。
高见:在唐启华的著作中,威尔逊的主张大大激励了中国人,他的声望在中国很高。您怎么看?
徐国琦:我们的研究有一点交叉,但观点不完全一致。1914年到1918年的一战对中国来说是承前启后,非常重要。1912年,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他要步法国和美国的后尘,变成民国?你要看孙中山的内阁、袁世凯的内阁大部分是留学的学生,如外交官顾维钧是留美博士,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是留美幼童,袁世凯的心腹大员蔡廷干也是留美人士。在内阁成员里面,留美背景极强,中国人当时就是要更新换代,要步美国后尘。一战爆发后,1917年8月14号,中国对德奥宣战,是步美国后尘的,因为当时威尔逊作为中立国总统,呼吁全世界中立国仿效美国,而中国一直就想参战,正好等这个机会趁势而起。所以,威尔逊当时发表十四点,民族自觉、平等外交等等,对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事。正因为如此,威尔逊当时在中国被年轻人视为上帝,中国留学生到美国领馆去呼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他的一篇文章公开称威尔逊是世界上头号好人。毛泽东那时候还名不见传的,但是他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就想未来的中国跟美国如果是同盟,那所向披靡。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强的亲美情节。威尔逊当时所谓的新国际秩序对中国非常有诱惑力。
高见:关于蒲安臣,大多数中国读者不是特别熟悉。
徐国琦:1868年,中国第一个出使世界的使团的团长是美国人蒲安臣。他这个人非常好,1861年到1867年是美国对华公使,1867年他准备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总理衙门说,你能不能代表我们出使全世界,他答应了。所以,1868年中美之间第一个和平条约、平等条约是蒲安臣代中国签的。蒲安臣条约为什么平等?第一个它讲究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来往,自由移民、自由来往、自由求学。
蒲安臣是1868年代表中国,先到美国华盛顿跟他的前领导William Henry Seward(西华德)国务卿签的这个条约,然后就到英国、到法国、到德国,然后1870年死在俄国,死的时候49岁,是中国政府的外交官,中国政府的雇员。蒲安臣的墓就在与哈佛大学咫尺之遥的奥本山墓地,钱是中国人出的。
在这些例子中,中美之间没有对抗,当时中国人和美国人互相吸引、互相坦诚,另外也互相支持。
高见:上世纪,另外一个美国人约翰·杜威对中国影响也很大,胡适、冯友兰都是他的弟子。
徐国琦:另外,杜威的学生还有蒋廷黻、蒋梦麟、陶行知等,民国期间都是各方面的领袖。约翰·杜威1919年4月30号到中国,一直到1921年7月份才离开。因为杜威在中国这两年,对他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回到美国之后,他俨然变成了中国专家。1952年,杜威过世,1945年时他都还想到中国来调停国共。
高见:齐锡生、杨天石老师的书里面也有讲到,抗战时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中国比较友善,而蒋介石为何特别厌恶丘吉尔?
徐国琦:中国在一战是极贫极弱的,没人理。二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坚持,使得二战之后中国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当时大英帝国丘吉尔竭力反对,斯大林竭力反对,而美国坚持。因为美国人的坚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强之一,蒋介石当时自己都觉得这个地位变化太大了。一战时,中国是一个极贫极弱的国家,任人宰割,到二战成为四强之一。之所以如此,因为当时美国人不喜欢法国人,法国后来是五强。从中美关系看,这个是剪不断的关联,况且很多方面都是正面的。
高见:因为你是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国,从个人的思想史角度来说,你对美国的认识过程是怎样的?
徐国琦:第一,要从中国近代历史上看,最早的留学浪潮是中国官方组织的留美幼童。1872年,当时的美国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应该说不是首选,因为美国高校比不上欧洲,当时最好的高校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当时的哈佛大学不过是一个小的、不入流的学校。而中国的留美幼童都送到美国去。1872年留美幼童前往美国,1881年召回,120个人。比如说第一任民国总理唐绍仪,设计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刚才我说的蔡廷干也是。留下的一百多人,人人都是各行精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美国当时也是个弱国、穷国,因为1872年美国刚刚结束了内战,正在重建,政治不稳,经济落后,高校也不发达。但就在那种情况下,因为中国人对美国人一种天然的好感和信赖,就派过去。这是第一波留学浪潮。
美国一战时成为世界强国,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随着地位上涨,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个人看,过去中国人有几个误区,就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美国好像是中国的小老弟,但你反过头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有成文宪法最早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有共和国机制最早的一个,美国、法国。中国是1912年才有的。
高见:就你讲的这些,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庚款的退还。我看到特朗普在联合国的演讲,他说美国是向善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一点,您怎么看?
徐国琦:你说的退庚款也是美国人最先。1904至1905年间,梁诚曾敦促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减免部分未付足的庚子赔款。他劝说美国政府,当年庚款要的太多了,远远的超过实际需要,多余的要退回来,美国人接受了。在所有的列强里面,美国是第一个。后来其他国家在各种压力下也开始退,但是不了了之。美国的庚款最有影响,胡适他们都是庚款留学生,3000多人。这些人都是一代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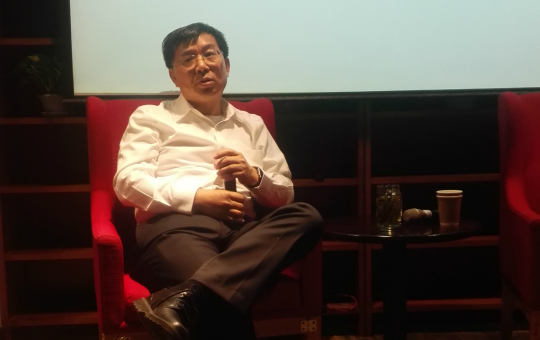
高见:有一段历史,我觉得现在研究的不多,就是黄安年先生出过一个《沉默的道钉》,原来的华工在美国给他们修铁路,然后我读过纳什主编的120万字的《我们人民》两卷本美国史,还有是方纳的《给我自由》两卷本美国史。我注意到里面的一个细节:在美国的这些中国华工,其实受到了很严重的歧视。您怎么看?
徐国琦:不仅是美国对华工歧视。整个从1882年,美国就通过排华法,在法律上歧视中国人。《沉默的道钉》黄安年先生做的非常好,因为这一段就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它做出来了,当时中国人去给美国人建太平洋铁路,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的财富是建立在中国铁路工人的血汗、生命里面。但这一段美国的确是这么多年来没有承认过。吉米·卡特当总统的时候,1979年表示感谢。但是这一段历史,我一直说哥伦比亚大学欠中国人的,就是华工给它修铁路。另外美国还有一个大学也欠中国人的,杜克大学。杜克本人是卖烟草起家的,当时卷烟机发明之后,他就对助手说把我的地球仪拿来,他一看中国人口那么多,如果让中国人都抽烟的话,那他赚多少钱?他能赚无数的钱!于是就向中国卖烟草,中国人的生气被他摧跨了对不对?但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
斯坦福大学最近才终于意识到它欠中国的,中美要联合研究这个题目,现在正在收集资料,因为资料没了,但现在资料很难收。像杜克先生的那些财务,中国人应该找出来或者是中美学者去看,究竟在中国赚了多少钱?你是怎么向中国人推销烟草的?这个不用说坏或者判断或者是要赔偿,我把这段历史给你还原过来,对不对?有很多的这种题目还要做。
《沉默的道钉》,黄安年先生做的非常好,但是资料现在还要进一步整理。因为要写一部好的学术著作,需要很多资料,但是现在非常遗憾,这些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他们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美国的文献资料也从来不重视,因为美国人当时歧视他们,留下的记录不多,现在一百多年之后,我们在想做这个题目,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斯坦福搞这个项目,因为我熟悉他们背景,现在很难做了,因为资料没了。资料没了,你就没法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可以写小说或者什么的,但是不是历史,所以黄安年先生那本书值得尊重。
高见:你自己做的中美共有的历史是求同。现在中美学者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你觉得它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徐国琦:实际上这个一直在做,在西方学者里面,某一个课题的研究很多,比如说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那都是大兵团作战,各方人马在写。它首先不强调你是中国学者、美国学者,看你有没有资格写,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就可以写,就像在2014年剑桥出了三卷版的一战国际史,谁是这个题目的权威,你就写,最后有几十个国家的学者就参与了。学术是不分国籍、不分宗教,就看你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能不能胜任,你写的东西是最尖端、最前沿、代表最新研究水平的。所以在这方面实际上一直在做。
过去我们写中美关系,比如说国内有一个陶文钊教授,他写了三卷本的《中美关系史》,2004年是第一版嘛,现在又出了一个修订本。我们都很熟。过去我们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强调中美对抗、强调中美分歧意识形态。像我刚才提到的中美关系,“共有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就从这个角度给你讲一段,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影响、互相启发的这一段历史。这个可能有的是正面、有的是负面,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像体育。中国体育全运会,实际上跟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系。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在天津设峰会,主要是美国人,然后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后来做过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的王正廷都是这里面来的,这就是体育,通过美国这个媒介过来。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来1984年洛杉矶洛杉矶奥运会上拿的第一块金牌。一些西方政要拒绝出席中国2008开幕式,小布什来了,还待了好几天,这个就是“共有历史”。
高见:最后一个问题,你手头写的第三部关于中国“共享的历史”,这本书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徐国琦:这个就是我的“共有历史”三部曲的最后一卷。第一卷是中美关系,第二卷是亚洲与大战,都是共有。第三部,我想与国内学者像葛兆光、台湾中研院学者王明珂,还有日本神户大学的王珂都在研究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因为他们这些人研究的主要是从中国谈中国,我要从国际的角度,打破国家民族的概念,从上面去看。
高见:从世界史的角度去看呢?
徐国琦:为什么?就像一个人,如果你不跟别人打交道,你叫什么?张三李四没关系。因为你要跟外面打交道。你是中国或者是中国人,所以你要跟其他国家要接触,跟其他人接触,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所以我要从古至今梳理“中国”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但现在我没法告诉你内容,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答案,还正在做。做完了、研究做完了,想法成熟了,可能才有个答案,现在没有答案。因为真正做历史的人,你不能先有答案,只能做完了才有答案。我就算现在告诉你一个答案,也有可能会被推翻,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当初做一战华工,我没有想到它的重要性,等我做完了,我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