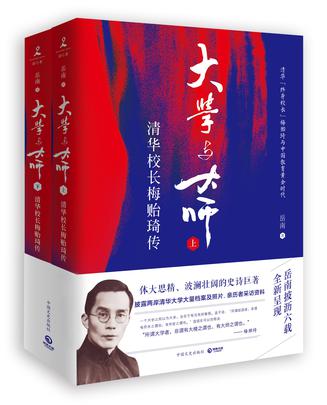编者按:作家岳南利用两岸清华大学的史料,加上采访、口述史、回忆录等资料,详述了清华大学的由来,以及梅贻琦与清华一生的情缘。近日,凤凰网专赴天津,采访了岳南。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张弘

凤凰网《高见》:此前,你的《南渡北归》《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等著作中,都有梅贻琦出场,但此番写作《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是作为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专门写作梅贻琦的传记。我想知道,这两个阶段,你对梅贻琦的认识和了解有何区别?
岳南:《大学与大师》这本书就是我解剖了一个学校和一个人。我有几点认识:第一点,对梅贻琦而言,通过梅贻琦的人生,从南开一直到清华,后来从清华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这个历程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在书中,尤其揭示了梅贻琦在没有当上校长之前这一段曲折的历程,他受的委屈,他经历的苦难,其中包括清华内部的纠葛,相互之间的斗争。
当时,圣约翰系和南开系这两个派系一直在争夺清华。特别像张彭春当了教务长之后,曹云祥收拾张彭春,曹要出国的时候,总共有30多人争夺校长职位,相互之间的角逐非常激烈,也非常热闹。要做清华校长,外交部得把住,老师得把住,学生还得把住,这三块都处好了,这个校长才能当上。
我感觉,梅贻琦的人格在读书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当了清华大学校长之后,政府明确命令要校长治校,但是他要教授治校,把权力放开,确实他是一个人格的体现。梅贻琦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他如果是不搞教授治校,就是要校长治校的的话,他能不能弄成?很难说。冯友兰引用蒋梦麟的话说,大学有三股势力,两股合力,第三股势力必然失败。他搞教授治校,一旦有事的时候跟教授一联合,学生必然失败。梅贻琦能够看清这个形势。另外,他本身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不贪污,不腐败。看他的日记,每天晚上吃吃喝喝,但没有往兜里塞钱。同时这个人理性,很清醒,一般的事不吭声。
第二,就是搞通识教育,这是他对清华非常大的功绩。
第三,他对各个方面关系处理很平和的,而且他没有多少私心,他没有一上来就组织自己的势力,原来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把事干好就好了。这样,可能就没有人反对他。
凤凰网《高见》: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已经有过很多校长,其中也有很用心做事的,人品也不错,但是都没有梅贻琦做的那么成功。除了刚才说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股势力的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岳南:有。除了三股势力之后,当时一个社会背景,就是五四运动起来之后,社会风潮是谁也不怕谁。其后革命兴起,像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军就起来了,整个形势就是谈革命。
那时候学生们很亢奋。国民党北伐,要利用学生势力,后来的共产党也要利用学生势力,这两个党一行动,学生就控制不住了。你弄一帮,我也弄一帮,后来的学生运动就不是学生运动了,实际就是两党运动。后来傅斯年就说,我非常不乐意把你们的学生运动跟五四相比,五四学生运动跟你们是不一样的,特别到了1947年、48年,傅斯年更恼火了,说什么纪念五四运动,你不要纪念了,你根本不是五四运动精神,你们这些学生,你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当时的大形势决定了这个事情。
凤凰网《高见》:你在书里面写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梅贻琦出身南开,是张伯苓的弟子,但是办校理念继承的却是蔡元培的办校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
岳南:我写《大学与大师》这个稿子,给清华大学校友、南加州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前副校长秦泗钊看,他打了一个问号,你怎么说他是按照蔡元培的理论办校呢?但是,梅贻琦在西南联大,在日记中批评闻一多的时候就说,闻一多这样做可能有点过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作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对共产主义颇为怀疑,我的办学理念就是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观点。这些话1946年讲的,我写的时候是他1931年当校长之后就这么办了,中间还差了十几年。为了打消读者的顾虑,我就专门在这儿专门加了一个小注释,他曾在日记中说过这句话。
张伯苓创办的南开,毕竟是一个私立学校,钱少,所以比较抠,在花钱少,还能够招人的科目上,有一点投机的心。国立学校就不一样了,要为整个国家考虑,为这个学科对人类的发展考虑,当然心胸就要开阔。一个人所在的位置,让人的格局和胸襟不一样。
另外,梅贻琦不仅是年轻,在西方接触了现代的文化,现代的社会风气,他的朋友,都是开现代文化风气之先的那些人,这两条就决定了他不能走张伯苓的路,必然要走蔡元培的路,兼容并包,文科和理工科并重。
还有一条,他在美国当留学生监督的时候,接触的面就更广了,不止是接触学生和一个学校,他就相当于一个教育部长,中国留学生当时已经派驻在美国的很多学校,他经常要跟美国教育部官员沟通,一起吃饭,一块谈事,这种接触带来的影响很大。
总之,这三点促使梅贻琦以自己独特风格执掌清华。要是没有这三点形成不了梅贻琦,那就形成不了清华当时兼容并包的教育。

凤凰网《高见》:之前,你在《南渡北归》里面,包括别的著作里面都写到了一点,梅贻琦在大陆执掌清华,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很发达,在当时也是大师云集,硕果累累。一般来说,理工科出身的校长,更容易忽视人文社会科学,但是梅贻琦非常重视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这里面有什么原因?
岳南:梅贻琦在美国留学、做留学生监督的时候已经看到,无论是理科还是工科,还是其他的科,没有文科仍然是缺一条腿,必须文理并重,美国教育基本上是这样的形式。梅贻琦已经看到了南开的不足,那些优秀的文科教授都跑了,张伯苓问李济说,你搞人类学有什么用呢?李济说什么用也没有,结果李济离开了,像吴大猷,饶毓泰等搞物理都从南开跑到北大、清华去了。
后来,何廉取代张伯苓当了南开的代理校长,他和张伯苓的关系很好,但是何廉还是说,我这个老师很好,但脑子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梅贻琦跟何廉、李济等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当然知道文科的重要。梅贻琦文理并重,后来很快就看到了成果。他很快就看到了南开的衰落。到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人数比例是7:5:2。人由于南开是私立大学,钱少,人少,这个不重要,你看看专家就行了,南开大学无非有一个化学系的杨石先,还有几个巨头,但是这几个巨头没有办法跟北大、清华比,理工科也没有比,特别是文科更不能比。这证明梅贻琦的路子是对的,他有可能吸取了南开的教训,吸收了美国的经验。
凤凰网《高见》:但是,《大学与大师》显示,他晚年在台湾重新办清华大学的时候,是先从原子能研究所开始来办的,放弃了人文社会科学这块,这主要出于什么原因?
岳南:当时,美国使用原子弹大家都很害怕。考古学家李济是中央博物院院长,当时中央博物院迁到李庄去了,他把同事叫来说,我们要用科学的眼光,要迎接原子时代的到来。
不久,白宫发表了关于“曼哈顿计划”的详细报告。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秘密筹划研制原子弹。俞大维建议由当时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担任原子弹计划的专家核心,人才名单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这批年轻学子,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美国政府以原子技术对外国保密为由,拒绝接收。吴大猷和华罗庚不得不请这些学子自寻出路。于是,唐敖庆被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李政道和朱光亚选择到密歇根大学学习核物理实验。
梅贻琦在台湾重新创建清华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放弃文科?因为梅贻琦先生当年留学的时候,本身是学理工科的,他弄不了文科,他可能跟理工科的人走得更近一点,而1948年到美国去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他在美国接触的那些人,像吴大猷等等全是理工科的。上世纪50年代,1955年、56年过去一批人,都已经投奔到台大去了。后来人家又创办文化学院等等,他没有空间,没有办法了,他只有办这个研究院所,别人不能竞争。
凤凰网《高见》:刚才我们说到,在清华,教授是一股势力,学生是一股势力,校长是一股势力,梅贻琦能不能取得一方的支持,这是成功掌校的关键。但是,《大学与大师》显示,梅贻琦既得到了教授认可,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你前面写到的很多被赶走的校长,不是得罪了教授,就是得罪了学生。但是梅贻琦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办法,教授和学生基本上都认可他,其中原因何在?
岳南:先说我这个《大学与大师》,我写的时候考虑了很长时间,梅贻琦之前的10个校长写不写?写梅贻琦传你扯那么远,扯那前面十个校长干吗?如果不写的话,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如果我一开始就从他当了校长开始写,就没有一个对比。
拿梅贻琦之前的清华校长来说,像周诒春那个人还不错,但是毕竟老了,这个人得罪了当时主管清华的外交部,后来他就走了。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很霸气,要搞党委说了算,校长是二把手,你必须都得听我的。
梅贻琦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他和教授合作,加上他洁身自好,不拉帮结派,到了1931之后,清华已经没有帮,没有派了,南开派也罢,圣约翰派也罢,都过去了。此时,清华培养出来的学子都从美国回来,到清华任教了,梅贻琦出身南开,也是清华留学生,这种先天性的优势,使他就可以做到和平共处,他不会人为分这个派那个派,无事找事。他就任清华校长之后,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子,不贪污,而且洁身自好,没有拉帮结派,有什么事叫大家一块开会,民主决策。所以说那会儿教授会也会支持他,大权还是在他手里的,他不会为了得罪教授会,去讨好某一个人。但是像前面几个校长,宁可得罪教授会也要把某一个人提上来,这就是梅贻琦能够在清华校长位置上待住的原因。
凤凰网《高见》: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教育史上的里程碑,这一成果梅贻琦有直接的关系,《大学与大师》里面写到一个细节,三校联合的时候,蒋梦麟做决定,把分校办到云南蒙自去了,梅贻琦心里面对此事很不赞成。而且蒋梦麟去蒙自分校的时候召集北大旧部聚会,一些北大教师就说不公平。刚才你也说到、西北联大,东南联大都没有成功,但是西南联大确实成功了,这里面梅贻琦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岳南:就写作来说,矛盾不容易表达。成就和明显失误的东西,能够从史料上查得出来,恰恰这个矛盾很难找到。包括同事之间的矛盾,你都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这些东西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在看不见之中看得见,西南联大也是这个问题。你通过蛛丝马迹一点点找,梅贻琦日记里头,他不会写今天晚上我跟谁怎样怎样,以及前因后果,梅贻琦不是那样的人。如果胡适写日记,写的还比较多,有时候好看一些,毛病能够表现出来。梅贻琦用几句话写吃饭,打牌赢了多少钱,输了多少钱,喝了多少酒,喝醉没喝醉。所以,只能从回忆录和日记中的蛛丝马迹找出来,再查相关的资料推断和佐证。蒙自这个事情,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三个学校的排序不可能是南开、清华、北大,只能是北大、清华、南开。所以蒋梦麟说昆明确实也有困难,梅贻琦也只能同意而已。
当时实在没有地方,现在看来到大理是最好的,并且有两个学校已经搬到那儿去了,洱海北边还有一些寺庙,大理的那些寺庙都可以用的。但是办到蒙自,交通也不便,没有多少风光,不如大理好。后来办了半年就撤销了。梅贻琦不争权,那个烂摊子谁愿意收拾更好。北大因为经费问题出现矛盾,梅贻琦有了怨气,对北大的郑天挺说,让蒋梦麟当西南联大主席至少一年。因为当时经费太少,导致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得找一把手,其实很难,所以都不乐意当一把手。梅贻琦不当这个一把手还是清华的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让的,所以也避免了一些冲突。

凤凰网《高见》:也就是说,西南联大的成功,与梅贻琦的性格和人品有很大关系。
岳南:我想他这个人格力量还是伟大的。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梅贻琦兢兢业业,维持三校的平衡。以人员比例来说,当时清华是七,北大是五,南开是二,清华最大。三校联合,不能让清华感觉到吃亏,又不能让那两个学校觉得压倒了它们,这个事情平衡很难。
在人事方面,梅贻琦搞得很好,这个学校去个教务长,那个学校去个训导长,各个系主任基本上匹配都很好,唯独一个经费问题比较麻烦。因为清华本身有钱,北大和南开还得指着国民政府拨钱,事实上他们就产生了矛盾。最后蒋梦麟说,北大的经费独立,不合作了。所以梅贻琦处理这个问题上,当时有点火气,后来他就到国民政府说,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吧,三校就分开。我感觉到,梅贻琦这么多年来已经做到了极致。最后,梅贻琦还是维护了大局,但也没有光听陈立夫的话,有时候该顶还是得顶,对于陈立夫想控制西南联大,搞党化教育,尽管梅贻琦尽管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是他还是顶住了。
凤凰网《高见》:你在书里面提到一个细节,陈立夫在教育经费上搞平均分配,这对西南联大非常不利,因为西南联大是三所大学联合在一起。陈立夫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岳南:因为陈立夫不喜欢西南联大,他的势力不但没有打进去,还被西南联大教训一顿。作为教育部长,有一些事也不见得是多么刻意的打压,毕竟他和西南联大共属于一个政权,我不太喜欢你,我没有让你占到便宜,我按人头分,你怎么说出来的?事实上,相当于西南联大吃了一个哑巴亏。如果是西南联大跟陈立夫关系好的话,他觉得这个方式不合理,再调整一下,或者是想个什么方法补助一点。到西南联大后期,清华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机器制造一点小商品,公开打着清华服务社的牌子做生意,一个是想赚点钱,第二就是对抗陈立夫。
凤凰网《高见》:《大学与大师》有一个贡献,里面对于地下党怎么发动学生,怎么在学校组织各种游行活动等交代得很清楚。在1935年、1936年,以及西南联大的尾期,包括1946年,到1948年梅贻琦离开清华。清华的学生运动特别频繁,教育秩序完全被扰乱了。尽管梅贻琦是非常不喜欢这类学生运动。但是,一旦学生出什么事,他又尽量保护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做?
岳南:这就是爱学生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你不要瞎折腾,最后你还是出了事了还得保。这样做的人也不只是梅贻琦了,像其他的学校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那个年代的学生跟校长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亲情。五四运动是自发的,并且学生还很占优势,反对卖国,是爱国运动。后来政党政治兴起,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学生在监狱蹲着也不是事,家长来闹事,社会也在批评,也没有办法上课,梅贻琦还是尽量想平息这个事。
凤凰网《高见》: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积极的介入政治,梅贻琦对闻一多是很有看法的,而且当时闻一多开除刘文典的时候,梅贻琦是支持闻一多的,闻一多在政治上这么激进,梅贻琦对他还是包容了。我们知道,西南联大后期,教授分裂还是很明显的。姚从吾在西南联大组织了国民党的支部和三青团组织,但是没有领导权;中共地下党发动学生多次游行示威,梅贻琦是怎么看这个事?
岳南:梅贻琦在日记当中说,你的政治立场我不管,你该上课的上课,保持学校正常的秩序,把该干的活干完就好了,这是兼容并包的体现,如果实在搞不下去了就没有办法了。但梅贻琦毕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立清华大学,然后是国立西南联大,毕竟是国民党领导这个国家。尽管如此,但是梅贻琦尽量把它打造成一个国立大学,在党跟国之间往国这边靠,至少在表面上,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绝对不能进来搞党委领导,党委还命令校长。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维持秩序,让学生先上课是梅贻琦应该做的,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政府确实不对,校长也不希望学生整天在外面游行示威而不学习。
凤凰网《高见》:《大学与大师》显示,梅贻琦很巧妙地把握了一条底线。各种学生社团组织学生煽动游行,梅贻琦实际上很了解这些人,如果他搞一个名单出来,报告给国民党,将这些带头煽动闹事的人直接交给政府,对他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一直维持一条底线,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尽管他心里面不喜欢这些学生不好好学习,但他还是尽量的庇护他们。在北平的时候,国民政府都列出要抓捕学生的名单来了,但是,梅贻琦还是尽量保护了学生,这个选择和立场也是非常微妙。
岳南:因为宪法有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梅贻琦希望,学生们尽量在行使权利的基础上别闹出更大的事来,一是别被打死了,别被抓进监狱;二是别跟政府对抗太厉害,把学校解散了。他希望维护学生的自由,又保证学生的生命安全,他就在中间做这些工作。所以,他确实是不容易。一般的学校,学生出去闹事,打死就打死了吧,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打死了几十个学生。胡适不是说吗?这一段我们太不管事了,我们的学生到处跑,最后跑到地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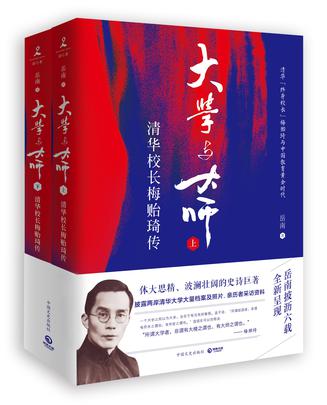
凤凰网《高见》:梅贻琦曾经想过,清华复员后解聘闻一多。学生运动闹到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曾经考虑,把学校给解散了。此外,梅贻琦对政治也不完全是隔绝的,他觉得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把专业学好了,报效国家,他主张是这种报国方式。抗战期间,他也支持很多学生参军,给美军做翻译。他这种爱国心,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理性和广阔的爱国主义,你对此怎么看?
岳南:梅贻琦对国家是非常爱,他爱的不见得是国民政府那批人,像傅斯年就说,目前只有国民党有力量组织政府,这是第一。第二,我支持政府,并不是代表着我支持贪官污吏。在那个年代,梅贻琦等很多人跟傅斯年的心理差不多,只是他没有写出来,傅斯年写出来了而已。
凤凰网《高见》:梅贻琦1948年年底很决然的就离开了大陆。梅贻琦离开大陆,主要是因为政治立场,或者说他还有别的更多的考量?
岳南:当时,周恩来说过,梅贻琦先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我们共产党的事,他可以留下来。但是后来梅贻琦还是走了,他走的时候说,我留下一个是做傀儡,一个是做反革命,这两条都是我不愿意做的,所以我要走。
梅贻琦一开始要到台湾去的,但是后来他没有去成,他才到美国去,把清华的基金保护起来,最终还是想跟着国民政府走。他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引用过孟子的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他还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已经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像鸟恋巢一样,他这个人恋旧,国民政府对他不薄,所以他必然要跟着国民政府走,他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最终还是到了台湾。
其实,他的政治立场,从1931年他当校长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他必然要跟着国民政府走的。
凤凰网《高见》:晚年的梅贻琦真的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谋权,他也没有为后人谋一分钱的好处,而且自己没有任何积蓄,生活都困难,老伴韩咏华在美国为了生计,,62岁了还出去做工。梅贻琦的这种清廉丝毫不逊于海瑞。梅贻琦住院后,病房和胡适挨着,两个老朋友互相安慰,结果1964年2月24日胡适先去世,三个月后梅贻琦去世。而胡适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财产,没有房产。你认为,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民国这一代知识分子?
岳南:这一代人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晚清,然后就是北洋和民国时期。他们有一种民族情绪,这种情绪一个是恨晚清,你这么软弱无能。同时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崛起。随着晚清的崩裂,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们把自己作为新的国家的主人,它的宪法和条例保障公民权利,他们都觉得改天换地。所以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非常热爱。另外,他们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儒生,深受儒家传统的的影响。儒家提倡忠君爱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君不在了,国家还在,他们爱国还是正常的。
编者按:作家岳南利用两岸清华大学的史料,加上采访、口述史、回忆录等资料,详述了清华大学的由来,以及梅贻琦与清华一生的情缘。近日,凤凰网专赴天津,采访了岳南。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张弘

凤凰网《高见》:此前,你的《南渡北归》《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等著作中,都有梅贻琦出场,但此番写作《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是作为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专门写作梅贻琦的传记。我想知道,这两个阶段,你对梅贻琦的认识和了解有何区别?
岳南:《大学与大师》这本书就是我解剖了一个学校和一个人。我有几点认识:第一点,对梅贻琦而言,通过梅贻琦的人生,从南开一直到清华,后来从清华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这个历程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在书中,尤其揭示了梅贻琦在没有当上校长之前这一段曲折的历程,他受的委屈,他经历的苦难,其中包括清华内部的纠葛,相互之间的斗争。
当时,圣约翰系和南开系这两个派系一直在争夺清华。特别像张彭春当了教务长之后,曹云祥收拾张彭春,曹要出国的时候,总共有30多人争夺校长职位,相互之间的角逐非常激烈,也非常热闹。要做清华校长,外交部得把住,老师得把住,学生还得把住,这三块都处好了,这个校长才能当上。
我感觉,梅贻琦的人格在读书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当了清华大学校长之后,政府明确命令要校长治校,但是他要教授治校,把权力放开,确实他是一个人格的体现。梅贻琦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他如果是不搞教授治校,就是要校长治校的的话,他能不能弄成?很难说。冯友兰引用蒋梦麟的话说,大学有三股势力,两股合力,第三股势力必然失败。他搞教授治校,一旦有事的时候跟教授一联合,学生必然失败。梅贻琦能够看清这个形势。另外,他本身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不贪污,不腐败。看他的日记,每天晚上吃吃喝喝,但没有往兜里塞钱。同时这个人理性,很清醒,一般的事不吭声。
第二,就是搞通识教育,这是他对清华非常大的功绩。
第三,他对各个方面关系处理很平和的,而且他没有多少私心,他没有一上来就组织自己的势力,原来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把事干好就好了。这样,可能就没有人反对他。
凤凰网《高见》: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已经有过很多校长,其中也有很用心做事的,人品也不错,但是都没有梅贻琦做的那么成功。除了刚才说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股势力的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岳南:有。除了三股势力之后,当时一个社会背景,就是五四运动起来之后,社会风潮是谁也不怕谁。其后革命兴起,像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军就起来了,整个形势就是谈革命。
那时候学生们很亢奋。国民党北伐,要利用学生势力,后来的共产党也要利用学生势力,这两个党一行动,学生就控制不住了。你弄一帮,我也弄一帮,后来的学生运动就不是学生运动了,实际就是两党运动。后来傅斯年就说,我非常不乐意把你们的学生运动跟五四相比,五四学生运动跟你们是不一样的,特别到了1947年、48年,傅斯年更恼火了,说什么纪念五四运动,你不要纪念了,你根本不是五四运动精神,你们这些学生,你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当时的大形势决定了这个事情。
凤凰网《高见》:你在书里面写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梅贻琦出身南开,是张伯苓的弟子,但是办校理念继承的却是蔡元培的办校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
岳南:我写《大学与大师》这个稿子,给清华大学校友、南加州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前副校长秦泗钊看,他打了一个问号,你怎么说他是按照蔡元培的理论办校呢?但是,梅贻琦在西南联大,在日记中批评闻一多的时候就说,闻一多这样做可能有点过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作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对共产主义颇为怀疑,我的办学理念就是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观点。这些话1946年讲的,我写的时候是他1931年当校长之后就这么办了,中间还差了十几年。为了打消读者的顾虑,我就专门在这儿专门加了一个小注释,他曾在日记中说过这句话。
张伯苓创办的南开,毕竟是一个私立学校,钱少,所以比较抠,在花钱少,还能够招人的科目上,有一点投机的心。国立学校就不一样了,要为整个国家考虑,为这个学科对人类的发展考虑,当然心胸就要开阔。一个人所在的位置,让人的格局和胸襟不一样。
另外,梅贻琦不仅是年轻,在西方接触了现代的文化,现代的社会风气,他的朋友,都是开现代文化风气之先的那些人,这两条就决定了他不能走张伯苓的路,必然要走蔡元培的路,兼容并包,文科和理工科并重。
还有一条,他在美国当留学生监督的时候,接触的面就更广了,不止是接触学生和一个学校,他就相当于一个教育部长,中国留学生当时已经派驻在美国的很多学校,他经常要跟美国教育部官员沟通,一起吃饭,一块谈事,这种接触带来的影响很大。
总之,这三点促使梅贻琦以自己独特风格执掌清华。要是没有这三点形成不了梅贻琦,那就形成不了清华当时兼容并包的教育。

凤凰网《高见》:之前,你在《南渡北归》里面,包括别的著作里面都写到了一点,梅贻琦在大陆执掌清华,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很发达,在当时也是大师云集,硕果累累。一般来说,理工科出身的校长,更容易忽视人文社会科学,但是梅贻琦非常重视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这里面有什么原因?
岳南:梅贻琦在美国留学、做留学生监督的时候已经看到,无论是理科还是工科,还是其他的科,没有文科仍然是缺一条腿,必须文理并重,美国教育基本上是这样的形式。梅贻琦已经看到了南开的不足,那些优秀的文科教授都跑了,张伯苓问李济说,你搞人类学有什么用呢?李济说什么用也没有,结果李济离开了,像吴大猷,饶毓泰等搞物理都从南开跑到北大、清华去了。
后来,何廉取代张伯苓当了南开的代理校长,他和张伯苓的关系很好,但是何廉还是说,我这个老师很好,但脑子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梅贻琦跟何廉、李济等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当然知道文科的重要。梅贻琦文理并重,后来很快就看到了成果。他很快就看到了南开的衰落。到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人数比例是7:5:2。人由于南开是私立大学,钱少,人少,这个不重要,你看看专家就行了,南开大学无非有一个化学系的杨石先,还有几个巨头,但是这几个巨头没有办法跟北大、清华比,理工科也没有比,特别是文科更不能比。这证明梅贻琦的路子是对的,他有可能吸取了南开的教训,吸收了美国的经验。
凤凰网《高见》:但是,《大学与大师》显示,他晚年在台湾重新办清华大学的时候,是先从原子能研究所开始来办的,放弃了人文社会科学这块,这主要出于什么原因?
岳南:当时,美国使用原子弹大家都很害怕。考古学家李济是中央博物院院长,当时中央博物院迁到李庄去了,他把同事叫来说,我们要用科学的眼光,要迎接原子时代的到来。
不久,白宫发表了关于“曼哈顿计划”的详细报告。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秘密筹划研制原子弹。俞大维建议由当时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担任原子弹计划的专家核心,人才名单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这批年轻学子,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美国政府以原子技术对外国保密为由,拒绝接收。吴大猷和华罗庚不得不请这些学子自寻出路。于是,唐敖庆被推荐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李政道和朱光亚选择到密歇根大学学习核物理实验。
梅贻琦在台湾重新创建清华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放弃文科?因为梅贻琦先生当年留学的时候,本身是学理工科的,他弄不了文科,他可能跟理工科的人走得更近一点,而1948年到美国去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他在美国接触的那些人,像吴大猷等等全是理工科的。上世纪50年代,1955年、56年过去一批人,都已经投奔到台大去了。后来人家又创办文化学院等等,他没有空间,没有办法了,他只有办这个研究院所,别人不能竞争。
凤凰网《高见》:刚才我们说到,在清华,教授是一股势力,学生是一股势力,校长是一股势力,梅贻琦能不能取得一方的支持,这是成功掌校的关键。但是,《大学与大师》显示,梅贻琦既得到了教授认可,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你前面写到的很多被赶走的校长,不是得罪了教授,就是得罪了学生。但是梅贻琦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办法,教授和学生基本上都认可他,其中原因何在?
岳南:先说我这个《大学与大师》,我写的时候考虑了很长时间,梅贻琦之前的10个校长写不写?写梅贻琦传你扯那么远,扯那前面十个校长干吗?如果不写的话,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如果我一开始就从他当了校长开始写,就没有一个对比。
拿梅贻琦之前的清华校长来说,像周诒春那个人还不错,但是毕竟老了,这个人得罪了当时主管清华的外交部,后来他就走了。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很霸气,要搞党委说了算,校长是二把手,你必须都得听我的。
梅贻琦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他和教授合作,加上他洁身自好,不拉帮结派,到了1931之后,清华已经没有帮,没有派了,南开派也罢,圣约翰派也罢,都过去了。此时,清华培养出来的学子都从美国回来,到清华任教了,梅贻琦出身南开,也是清华留学生,这种先天性的优势,使他就可以做到和平共处,他不会人为分这个派那个派,无事找事。他就任清华校长之后,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子,不贪污,而且洁身自好,没有拉帮结派,有什么事叫大家一块开会,民主决策。所以说那会儿教授会也会支持他,大权还是在他手里的,他不会为了得罪教授会,去讨好某一个人。但是像前面几个校长,宁可得罪教授会也要把某一个人提上来,这就是梅贻琦能够在清华校长位置上待住的原因。
凤凰网《高见》: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教育史上的里程碑,这一成果梅贻琦有直接的关系,《大学与大师》里面写到一个细节,三校联合的时候,蒋梦麟做决定,把分校办到云南蒙自去了,梅贻琦心里面对此事很不赞成。而且蒋梦麟去蒙自分校的时候召集北大旧部聚会,一些北大教师就说不公平。刚才你也说到、西北联大,东南联大都没有成功,但是西南联大确实成功了,这里面梅贻琦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岳南:就写作来说,矛盾不容易表达。成就和明显失误的东西,能够从史料上查得出来,恰恰这个矛盾很难找到。包括同事之间的矛盾,你都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这些东西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在看不见之中看得见,西南联大也是这个问题。你通过蛛丝马迹一点点找,梅贻琦日记里头,他不会写今天晚上我跟谁怎样怎样,以及前因后果,梅贻琦不是那样的人。如果胡适写日记,写的还比较多,有时候好看一些,毛病能够表现出来。梅贻琦用几句话写吃饭,打牌赢了多少钱,输了多少钱,喝了多少酒,喝醉没喝醉。所以,只能从回忆录和日记中的蛛丝马迹找出来,再查相关的资料推断和佐证。蒙自这个事情,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三个学校的排序不可能是南开、清华、北大,只能是北大、清华、南开。所以蒋梦麟说昆明确实也有困难,梅贻琦也只能同意而已。
当时实在没有地方,现在看来到大理是最好的,并且有两个学校已经搬到那儿去了,洱海北边还有一些寺庙,大理的那些寺庙都可以用的。但是办到蒙自,交通也不便,没有多少风光,不如大理好。后来办了半年就撤销了。梅贻琦不争权,那个烂摊子谁愿意收拾更好。北大因为经费问题出现矛盾,梅贻琦有了怨气,对北大的郑天挺说,让蒋梦麟当西南联大主席至少一年。因为当时经费太少,导致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得找一把手,其实很难,所以都不乐意当一把手。梅贻琦不当这个一把手还是清华的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让的,所以也避免了一些冲突。

凤凰网《高见》:也就是说,西南联大的成功,与梅贻琦的性格和人品有很大关系。
岳南:我想他这个人格力量还是伟大的。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梅贻琦兢兢业业,维持三校的平衡。以人员比例来说,当时清华是七,北大是五,南开是二,清华最大。三校联合,不能让清华感觉到吃亏,又不能让那两个学校觉得压倒了它们,这个事情平衡很难。
在人事方面,梅贻琦搞得很好,这个学校去个教务长,那个学校去个训导长,各个系主任基本上匹配都很好,唯独一个经费问题比较麻烦。因为清华本身有钱,北大和南开还得指着国民政府拨钱,事实上他们就产生了矛盾。最后蒋梦麟说,北大的经费独立,不合作了。所以梅贻琦处理这个问题上,当时有点火气,后来他就到国民政府说,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吧,三校就分开。我感觉到,梅贻琦这么多年来已经做到了极致。最后,梅贻琦还是维护了大局,但也没有光听陈立夫的话,有时候该顶还是得顶,对于陈立夫想控制西南联大,搞党化教育,尽管梅贻琦尽管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是他还是顶住了。
凤凰网《高见》:你在书里面提到一个细节,陈立夫在教育经费上搞平均分配,这对西南联大非常不利,因为西南联大是三所大学联合在一起。陈立夫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岳南:因为陈立夫不喜欢西南联大,他的势力不但没有打进去,还被西南联大教训一顿。作为教育部长,有一些事也不见得是多么刻意的打压,毕竟他和西南联大共属于一个政权,我不太喜欢你,我没有让你占到便宜,我按人头分,你怎么说出来的?事实上,相当于西南联大吃了一个哑巴亏。如果是西南联大跟陈立夫关系好的话,他觉得这个方式不合理,再调整一下,或者是想个什么方法补助一点。到西南联大后期,清华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机器制造一点小商品,公开打着清华服务社的牌子做生意,一个是想赚点钱,第二就是对抗陈立夫。
凤凰网《高见》:《大学与大师》有一个贡献,里面对于地下党怎么发动学生,怎么在学校组织各种游行活动等交代得很清楚。在1935年、1936年,以及西南联大的尾期,包括1946年,到1948年梅贻琦离开清华。清华的学生运动特别频繁,教育秩序完全被扰乱了。尽管梅贻琦是非常不喜欢这类学生运动。但是,一旦学生出什么事,他又尽量保护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做?
岳南:这就是爱学生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你不要瞎折腾,最后你还是出了事了还得保。这样做的人也不只是梅贻琦了,像其他的学校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那个年代的学生跟校长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亲情。五四运动是自发的,并且学生还很占优势,反对卖国,是爱国运动。后来政党政治兴起,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学生在监狱蹲着也不是事,家长来闹事,社会也在批评,也没有办法上课,梅贻琦还是尽量想平息这个事。
凤凰网《高见》: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积极的介入政治,梅贻琦对闻一多是很有看法的,而且当时闻一多开除刘文典的时候,梅贻琦是支持闻一多的,闻一多在政治上这么激进,梅贻琦对他还是包容了。我们知道,西南联大后期,教授分裂还是很明显的。姚从吾在西南联大组织了国民党的支部和三青团组织,但是没有领导权;中共地下党发动学生多次游行示威,梅贻琦是怎么看这个事?
岳南:梅贻琦在日记当中说,你的政治立场我不管,你该上课的上课,保持学校正常的秩序,把该干的活干完就好了,这是兼容并包的体现,如果实在搞不下去了就没有办法了。但梅贻琦毕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立清华大学,然后是国立西南联大,毕竟是国民党领导这个国家。尽管如此,但是梅贻琦尽量把它打造成一个国立大学,在党跟国之间往国这边靠,至少在表面上,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绝对不能进来搞党委领导,党委还命令校长。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维持秩序,让学生先上课是梅贻琦应该做的,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政府确实不对,校长也不希望学生整天在外面游行示威而不学习。
凤凰网《高见》:《大学与大师》显示,梅贻琦很巧妙地把握了一条底线。各种学生社团组织学生煽动游行,梅贻琦实际上很了解这些人,如果他搞一个名单出来,报告给国民党,将这些带头煽动闹事的人直接交给政府,对他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一直维持一条底线,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尽管他心里面不喜欢这些学生不好好学习,但他还是尽量的庇护他们。在北平的时候,国民政府都列出要抓捕学生的名单来了,但是,梅贻琦还是尽量保护了学生,这个选择和立场也是非常微妙。
岳南:因为宪法有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梅贻琦希望,学生们尽量在行使权利的基础上别闹出更大的事来,一是别被打死了,别被抓进监狱;二是别跟政府对抗太厉害,把学校解散了。他希望维护学生的自由,又保证学生的生命安全,他就在中间做这些工作。所以,他确实是不容易。一般的学校,学生出去闹事,打死就打死了吧,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打死了几十个学生。胡适不是说吗?这一段我们太不管事了,我们的学生到处跑,最后跑到地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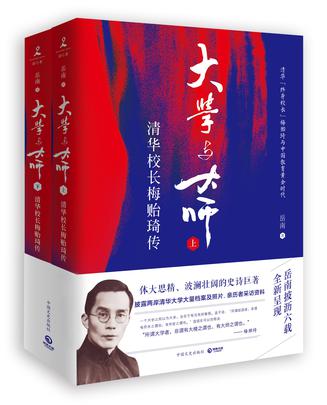
凤凰网《高见》:梅贻琦曾经想过,清华复员后解聘闻一多。学生运动闹到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曾经考虑,把学校给解散了。此外,梅贻琦对政治也不完全是隔绝的,他觉得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把专业学好了,报效国家,他主张是这种报国方式。抗战期间,他也支持很多学生参军,给美军做翻译。他这种爱国心,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理性和广阔的爱国主义,你对此怎么看?
岳南:梅贻琦对国家是非常爱,他爱的不见得是国民政府那批人,像傅斯年就说,目前只有国民党有力量组织政府,这是第一。第二,我支持政府,并不是代表着我支持贪官污吏。在那个年代,梅贻琦等很多人跟傅斯年的心理差不多,只是他没有写出来,傅斯年写出来了而已。
凤凰网《高见》:梅贻琦1948年年底很决然的就离开了大陆。梅贻琦离开大陆,主要是因为政治立场,或者说他还有别的更多的考量?
岳南:当时,周恩来说过,梅贻琦先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我们共产党的事,他可以留下来。但是后来梅贻琦还是走了,他走的时候说,我留下一个是做傀儡,一个是做反革命,这两条都是我不愿意做的,所以我要走。
梅贻琦一开始要到台湾去的,但是后来他没有去成,他才到美国去,把清华的基金保护起来,最终还是想跟着国民政府走。他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引用过孟子的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他还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已经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像鸟恋巢一样,他这个人恋旧,国民政府对他不薄,所以他必然要跟着国民政府走,他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最终还是到了台湾。
其实,他的政治立场,从1931年他当校长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他必然要跟着国民政府走的。
凤凰网《高见》:晚年的梅贻琦真的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谋权,他也没有为后人谋一分钱的好处,而且自己没有任何积蓄,生活都困难,老伴韩咏华在美国为了生计,,62岁了还出去做工。梅贻琦的这种清廉丝毫不逊于海瑞。梅贻琦住院后,病房和胡适挨着,两个老朋友互相安慰,结果1964年2月24日胡适先去世,三个月后梅贻琦去世。而胡适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财产,没有房产。你认为,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民国这一代知识分子?
岳南:这一代人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晚清,然后就是北洋和民国时期。他们有一种民族情绪,这种情绪一个是恨晚清,你这么软弱无能。同时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崛起。随着晚清的崩裂,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们把自己作为新的国家的主人,它的宪法和条例保障公民权利,他们都觉得改天换地。所以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非常热爱。另外,他们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儒生,深受儒家传统的的影响。儒家提倡忠君爱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君不在了,国家还在,他们爱国还是正常的。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